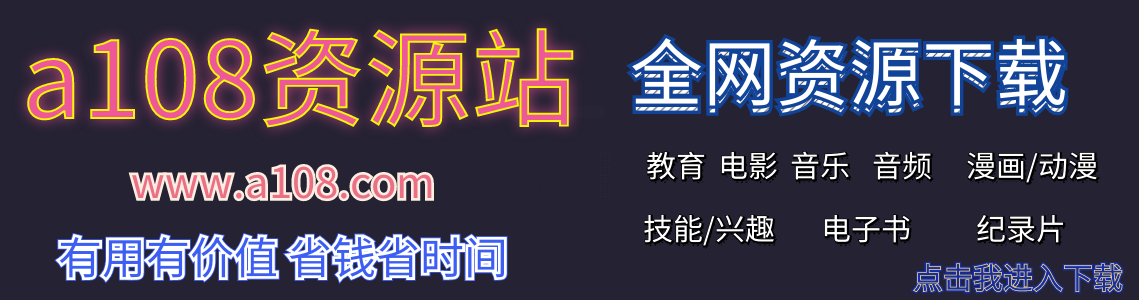通信公司二电台是全连唯一一个用电传通信的电台,俗称“单边带”。我从73团无线电报训练队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单边带电台。
单边乐队(左起,前排吕秋生、牟,后排刘宗博、张宪春、黄、陈洁芳
单边带是什么?听起来很奇怪。单边带电台是“只使用两个边带中的一个边带信号来发射和接收调幅信号”的无线电通信装置,英文“SSB”。单边带通信的优点是:节省频带,省电,保密性高。虽然单边带在国外已经发明和使用了几十年,但作为军用电台的中国还是一项新技术。相比公司其他电台,我们的单边带还是比较先进的,因为我们用的是电传,收发快,看得见,抗干扰能力强。第一,学会用电传单边带。主要通信手段是电传,学习使用电传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单边带无线电报务员的必修课。当年,我们通信站能掌握电传技术的有20多人。除了我们电报局2的报务员,内勤站有线电报局的女兵也知道这个技术。学习电传,说白了就是学习打字。就像今天在电脑前打字一样,没有什么新意。不同的是,今天我们的打字主要是以汉语拼音或者英文字母为主,SSB操作员的培训主要是以练习打阿拉伯数字为主。因为所有电报都是基于阿拉伯数字的。今天,我们正以各种姿势在电脑前打字,键盘上与手指对应的字母或数字是任意的。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字,而且你是自由的。当电传操作员是不可接受的。为了快速准确地交流,操作者必须从一开始就练习基本功,正确使用击打位置和击打力度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会形成一种慢性动作,以后很难纠正,打字速度和准确度都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在电脑前打字。大部分人都在看键盘和屏幕,有些人还在看稿子。他们的眼睛上下翻飞,东张西望,很着急。如果你让他不看键盘盲目打字,估计十个人有九个打不出来或者一次次出错。我们的电传操作员学习打字,我们从第一天起就盲目打字。打字时只能看电报草稿,不能看键盘,也不能看打出来的电报。只有当你发现你可能打错了一个错别字时,你才被允许阅读信息。为什么盲打键盘不能有错误?因为我们十个手指中有九个参与敲键盘,而且具体分工明确。每个手指固定一个或两个键盘,不移位,不连号,保证了打字的准确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传打字机
1973年,集训队分成三个人,我、江西的陈海平和福建武平的李永忠。来到单边带,先学会电传。当时国安局的局长是湖南兵张献春。他的电传技术高超,成了我们电传培训班的老师。于是,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三个人开始噼里啪啦地学习打字。巧合的是,在我们培训的当天,我们培训队的前女学员,后台站有线台的畅畅和小燕也加入了我们的电传培训。因为后台站有线台的操作员也必须掌握电传打字的技能,有线台领导走了一条捷径,把两个女兵交给有线台统一培训。反正一只羊在开,一群羊也在开。熟悉了这一点,就会事半功倍。看他们多聪明。小小的教室里,只有五个学生,第一排两个女兵,第二排三个男兵。两位女学员在训练中显得很用心,很勤奋,很努力。培训期间,除了和张老师交流,就是打字,打字,默默打字。大概是想和我们男兵比一比。
两名学习电传的女兵。
学习电传相对于学习手钥匙来说是比较简单容易的,重点是手、脑、眼的配合。怎么配合都不会多余。现在,每个人都会打字。打字不再是一种技能,而是人们工作生活的必需品,就像中国人吃饭可以用筷子一样。电传最基本的要求是快速、准确和稳定。是快速合格的电传操作员,考核必须达到每分钟70组代码280个字符;每次连续打字20分钟,不少于1400组,共5600字。间隔用4个字符,回车用10组代码,换页用100组代码。这样,你必须每秒钟打6个字符以上。所以,争分夺秒,急不得,成了我们每个电传操作员的基本功。我们换页不是把打好的信息轻轻放在桌子上,而是把它们扔到天上,让它们慢慢落下,就0.5秒左右。以至于考完试,10多页的留言像仙女花一样掉了一地。准确性是指在考核中,5600字错误中有一项不及格,这是非常严格的。我在文章《塔子山上报训队》里提到过,对于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来说,错误的代码是绝对不允许的,无论是发报还是抄报。像电传一样,输入的字符就是发送的代码。不允许有任何错误。一旦犯错,后果不言而喻。打错字如果发现可以纠正,5600字。纠正一个好,纠正两个通过,纠正三个。如果你失败了,你会和我们在一起。所以从新电传操作员开始,一定要坚持不出错,习惯了,久而久之不出错或少出错。后来我们在单边带工作的时候,刘宗波、陆秋生、陈洁芳、牟这些顶尖的电传技术人员,都创造了10万套电传没有错误。10万组,40万字。好样的。容易吗?稳定性是对无线电操作员的基本要求。电传和手键传输一样,节奏清晰,流水潺潺,犹如春江。熟练的电传操作员基本上可以不停顿、不卡顿、不中断地打字,一条信息可以一气呵成地传递出去。还有的声音像潺潺流水,悦耳动听。2.夜班经过半年的收发报训练和两个多月的电传打字训练,我们几个新兵基本具备了值班条件,和老兵一起值班。值班就是按照固定的联络时间收发电报。当然,所有发送和接收的电报都是训练信息。当你成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你就开始值班了,就像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和电话总机的接线员一样。从此你基本上就没有“睡觉”的机会了。一年有365天,不管平时还是节假日,至少有一半时间,你只能睡半个晚上,另一半时间你都是在广播室度过的。一半的时间,你要么上夜班(晚上18: 00到凌晨1: 00),要么上夜班(凌晨1: 00到8: 00)。刚开始,新兵肯定觉得很不舒服。年轻人是睡觉的最好时机。想想看,“春困秋困,夏困冬不眠三月”。夜班比较好。吃完饭有人来接班,然后半夜1点有人来接班。下班后,他们会去食堂吃一碗面,马上回宿舍,倒头就睡。夜班是最辛苦的工作。部队一般晚上九点半熄灯,半夜十二点半睡得很香。突然,他们被无情地吵醒,迷迷糊糊地起床,不洗牙不刷牙地走向厨房。这会儿人就醒了,然后接班等早班来接你,一直到天亮。好在上完夜班,第二天早上是夜班规定的抓睡时间,可以好好睡一上午。
拥有单边电台的四兄弟(左起:我、李永忠、陆秋生、陈洁芳)
准时赶上很有趣。可以睡到午饭,也可以看书写信(除了值班时间收发电报,我们绝对禁止做任何无关的事情。我们宁愿让你发呆,也不愿让你看书写信)。那时候,我爱读书。只要有一本好书,即使我不睡觉,我也会读完它。只是连队的士兵不允许熬夜,熄灯后还要钻进被窝。早上睡觉的时间变成了学习的好时间。可惜文革时期,各种书籍少之又少,文学名著难觅。有时候遇到好书,僧多粥少,大家轮流读。自然,你没有多少时间了。你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发挥自己的阅读能力,尽最大努力完成。一旦我们有了好书,就是我们书迷赶夜班的最好时机。有一段时间我看的最多的是前苏联的小说,当然不是俄国时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样的名著。这些小说在那个年代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前苏联六七十年代的书,新出版的所谓“供批判”。我们公司有几个人才,经常能拿到这些前苏联的稀有小说。这些书一出现,马上就成了抢手货,私下在几个读书爱好小组中流传,尽可能不让指导老师徐去找。就这样,当年看了很多这样的书,好像有苏联现实主义小说,科切托夫的《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和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战争回忆录有朱可夫的《战争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亚历山大瓦迪斯劳的《在远东》。我很喜欢那些二战时期的作品。一旦我得到了他们,我很饿,很快就看到了他们。后来又陆续看了威廉谢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等等。看,从上夜班到看小说。正是因为上夜班,我才能挤出很多时间,无数的精神食粮才能被我吞下。我仍然反复咀嚼它们,回味无穷。
我和陈海平。
上夜班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吃一顿夜宵。我曾经在《发信台的故事》里提到过,上夜班的人,每晚的夜餐费是15分钱;还谈到发帖台没有食堂,只好自己买零食当夜宵。公司夜餐不如吃食堂煮的胡辣汤面。公司的伙食本来就不好,平时也很少吃面。夜班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绝对是一件让人神清气爽的事情。别看只是一碗面,只值0.15元,但做好却不容易。我们73岁的战士叫刘永龙,福建武平人,也是我们组无线电报务员之一。在食堂轮岗后,他做夜宵最有经验,做出来的挂面最香最好吃,有口皆碑。夜班如果你在夜班遇到他,你会很幸运。面条劲道,肉丝顺滑,汤面清香。然后,在汤里放一些从公司菜地里采摘的新鲜大蒜或小葱。顿时香味四溢,鼻端食欲大开。我至今不忘。第三,生产下到电报局单边带之后,我逐渐发现单边带在当时的电报局是绝对不一样的,不仅表现在业务上的差异,而且单边带的所有工作在电报局都是名列前茅的,而且榜上有名。无论人员素质,战备水平,军事训练等。都很好。即使他们从事生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个公司的生产好不好,蔬菜水果收获多少,猪圈里的猪肥不肥,是衡量一个公司整体工作的关键指标。所以公司下属单位的生产做得怎么样,也是评价各站工作优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单边带在电报局生产指数中名列前茅,无论是数量还是换算价格。我绝对不是吹牛大王。你看,李连给了我们塔子山上最好的大而平的菜地(电报局食堂前的菜地);连木匠每年都被请去箍桶,很多新桶送给我们;春天,李连派人去北峰砍竹子种豆子,我们台收获最多。总之,我们对公司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生产工具在我公司的配备给予了特别的考虑。公司生产没有奖励。唯一的奖励是每个站的生产和收入的季度评估会议。副站长何发如会召集全体人员,司务长胡海庚会公布全站和各站每季度生产的蔬菜总量和价格,以区别各站在生产上的成绩。当然,排名第一的人是光荣的,落后的人一定很关键。本质上,这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因为菜地大,土质好,管理好,再加上人多,精力充沛,工作努力,单边带每次评论总是排第一,第二名被拉得很远。有点像NBA球队的精湛球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篮球队基本都在后面。久而久之,其他站也失去了追赶我们两个生产目标的动力。
当年部队装备的“小八一”电台车就是北京212改装的。
杨建国的导演是湖南人,他非常喜欢吃辣椒,并且擅长种植辣椒。除了冬天,他们的菜地基本上都是辣椒。由于各种蔬菜都是采摘成熟后送到食堂,食堂工作人员会对各站送来的蔬菜进行称重登记,然后由食堂负责购买蔬菜,并根据当时的菜价以各站的名义进行登记。按照市场价格,辣椒是上等菜,总是比大白菜、萝卜、豆角贵,所以他们在台湾猛种辣椒。数量虽少,但经不起高价,事倍功半,有炒作之嫌。我们站的陈洁芳借用《南征北战》的一句台词对7站的人说,辣椒不能当菜吃,要靠我们的白菜萝卜解决问题!我不知道杨建国的谬论从何而来,所以他立即反驳它。没油能吃吗?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恢复过来。要问我们为什么单方面生产这么好,除了客观原因,还有一批很能干的同志。赵,河北军人,在家种菜,对种菜有很深的体会。同安陈洁芳虽然小,但是很勤快,给蔬菜打农药的脏活都是他干的。山东兵牟憨厚,是个好制片人。人们不愿意做的事,他都不在乎。来自江西的战士陈海平虽然没有干农活的经验,但他经常一个人在菜地里干活,有时还会去猪圈里挑猪粪,把我们单侧菜地里的粪坑填平。有这样一群特别能干的同志,为什么不在一边的菜地里开出五颜六色的菜花,结出累累硕果?
斜!